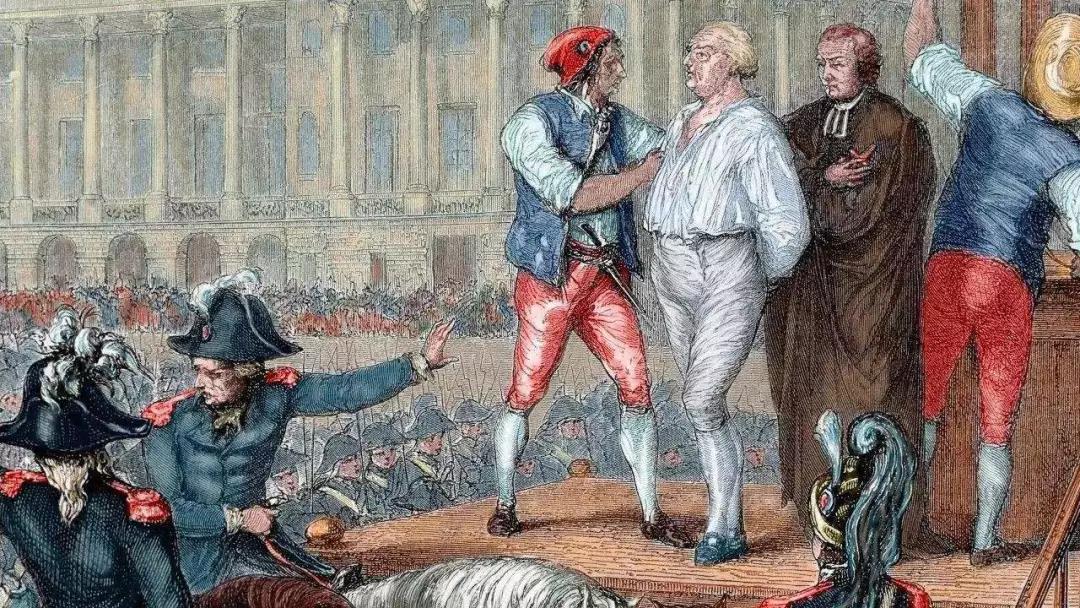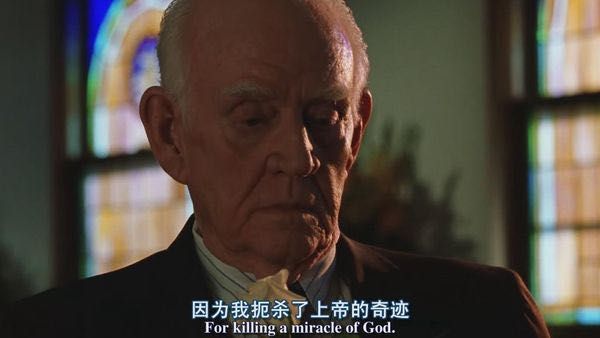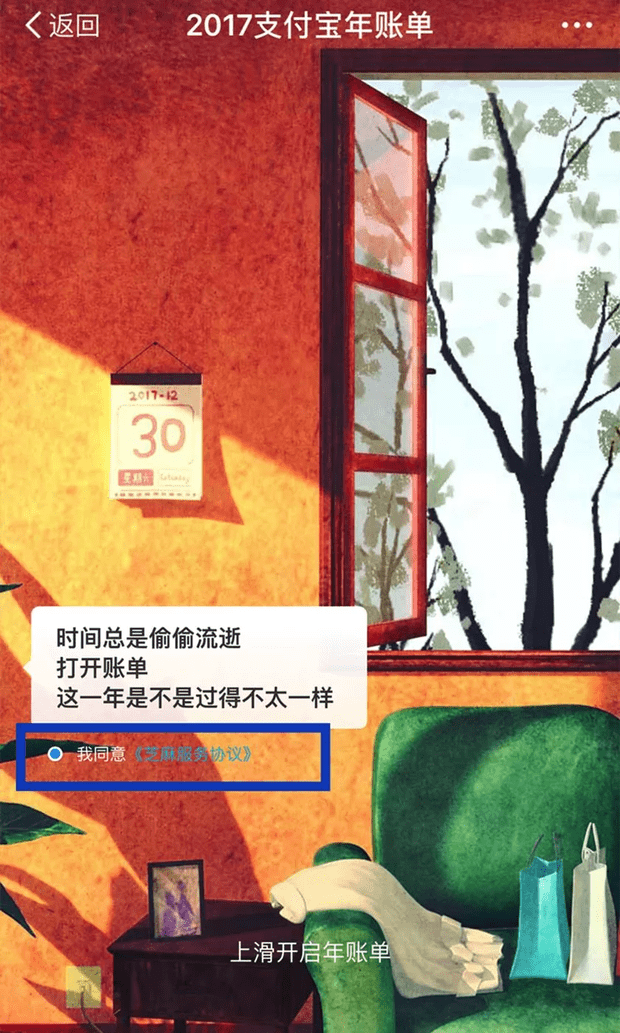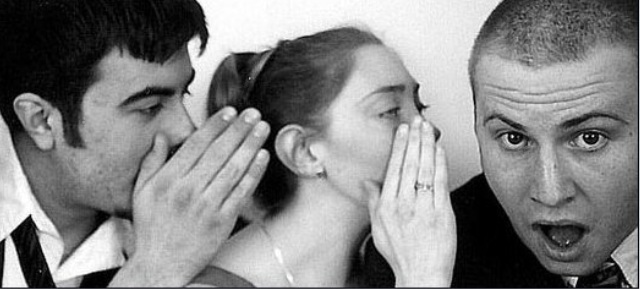就律师会见中录音、录像问题与青岛市看守所商榷
11月19日下午在青岛市看守所会见陈青沙起初,发生了一个插曲。
和之前会见一样,我拿出录音笔打开,开始和陈青沙交谈。不一会儿,一位领导模样的女民警(后来听说是所长或者副所长,下称民警)进入会见室,要求我把录音笔收起来,并说看守所有规定:不许律师在会见中使用通讯设备、不许录像、拍照。我说,录音笔不是通讯工具、也不是摄像机、照相机,它只是律师在有限的会见时间内为尽量多获取交谈信息所使用的一个工具。
民警又强调,录音笔应该收起来。我回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律师无权以录音方式记录会见内容,即便是我面前这张桌子上摆放的青岛市看守所现有的合法性有待商榷的律师会见规定中,也未禁止律师录音。
民警继续让我收起来,并说,如果我认为青岛市看守所现行规定没有禁止律师录音的话,她现在可以加上。我提高了声音回答:您仅仅是一名民警,就可以在律师会见过程中随意设置规定?您是在滥用职权,我不会遵守职权被滥用的情况下对我会见嫌疑人带来不利妨害的任何恶意规定。
民警接着说:你不必发火,也不必那么大声,我只是请你收起来。我再回答:我讲话声音大是因为对您的行为感到愤怒,您虽然始终小声讲话,但您的讲话内容明确向我传递出滥用权力的信息,既然您请我把录音笔收起来,那么,我拒绝您的请求。
谈话不欢而散,会见继续进行,我没有收录音笔。我已经第四次会见陈青沙了,每次会见都用录音笔记录会见内容,回京后再交给助理整理,我不能确定,在将来第五次会见陈青沙时,青岛市看守所的律师会见规定上是否会加上“禁止录音”。
关于律师会见中是否有权录音、录像(拍照)的问题,原本并不是问题,但因为一些看守所随意对律师会见设置规定的做法已成习惯,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全是问题。
关于录像(拍照)问题,我以为,除了嫌疑人(被告人)遭遇刑讯,有目视可见的外伤、为取证所需,或嫌疑人(被告人)有事先写好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需要律师以照片方式留存以供参考外,会见过程中拍摄嫌疑人照片并无意义。在平度陈宝成案律师团第一次抵达平度当晚讨论工作方案时,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认为,身穿囚服、坐在铁窗后的嫌疑人照片除了能吸引眼球、利于传播外,对律师办理案件并无任何实质帮助;虽然照片的传播不会对公安、检察机关案件侦办工作形成任何妨碍,但长期以来,公安部门已习惯固步自封,在律师会见过程中能否录像(拍照)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谨慎和敏感;适逢司法部正就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相关规定与最高检、最高院以及公安部磋商,为了让司法部好说话,应尽量避免刺激公安部门一贯敏感的神经。事实证明,有同仁并未听取我的建议,陈宝成案数名当事人身陷囹圄的照片在互联网广为传播。之后,我发现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原先已允许律师录音、录像(拍照)的北京市各看守所禁止律师录像(拍照),其他各地看守所类似的禁止性规定亦有出台。我没有就此问题再开口讲话。我认为,即便是律师,也应为自己不谨慎的工作方式付出代价。
但我坚持认为看守所不应禁止律师会见录音。《律师法》第10条第二款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经常办理外省市案件的律师相比警察、检察官、法官来说,会见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更为有限,虽然律师在会见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在大多情况下并不作为证据向办案机关提交,但尽可能多获取信息以制定行之有效的辩护方案是《刑诉法》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应有之意。以我的经验看,假定我会见了某个嫌疑人(被告人)两个小时,录音内容需要助理用两天时间去整理,可以打印几十页;但如果不录音仅书写笔录,两个小时最多就写几页纸。无论基于效率还是公平,会见过程中用录音方式记录交谈信息都有利于律师行使执业权进而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且,录音方式并不会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看守所的管理教育工作形成任何阻碍。这种情况下,一拍脑门就出台损人不利己的禁止录音的规定不仅不合理,更不合法。
撰此小文,不仅与青岛市看守所商榷、与更多公安部门商榷,更与所有法律人商榷。毕竟,对律师会见权利的任何影响都将最终表现为对公民财产、自由和生命权的保护或损害。
精彩推荐
- ·致中共赣州市委史文清书记的一封..2015-06-27
- ·致军委习主席的一封信2013-04-01
- ·就#衡阳周氏家族案#对衡阳中院..2015-11-27
- ·戴玉庆案:反腐还是报复?2015-06-05
- ·王甫:刑法修正案(九)或将导致..2015-08-29
- ·建三江困局2014-03-30
- ·司法打手 末路狂徒2012-08-31
- ·清明节悼念靖江司法2013-04-04
- ·致湖南高院康为民院长的一封信2014-03-27
- ·律师为谁辩护2019-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