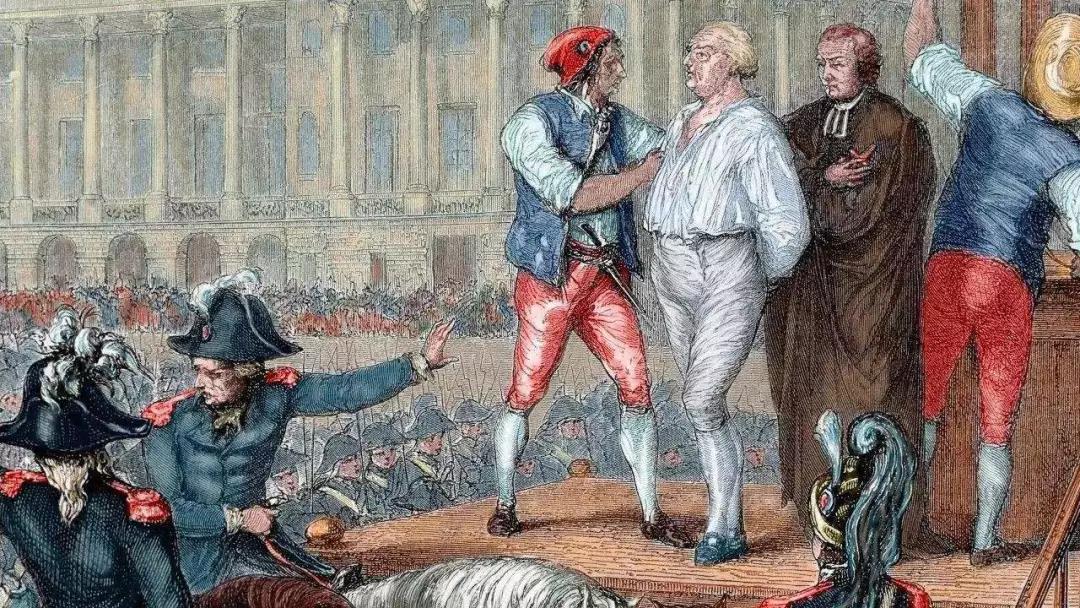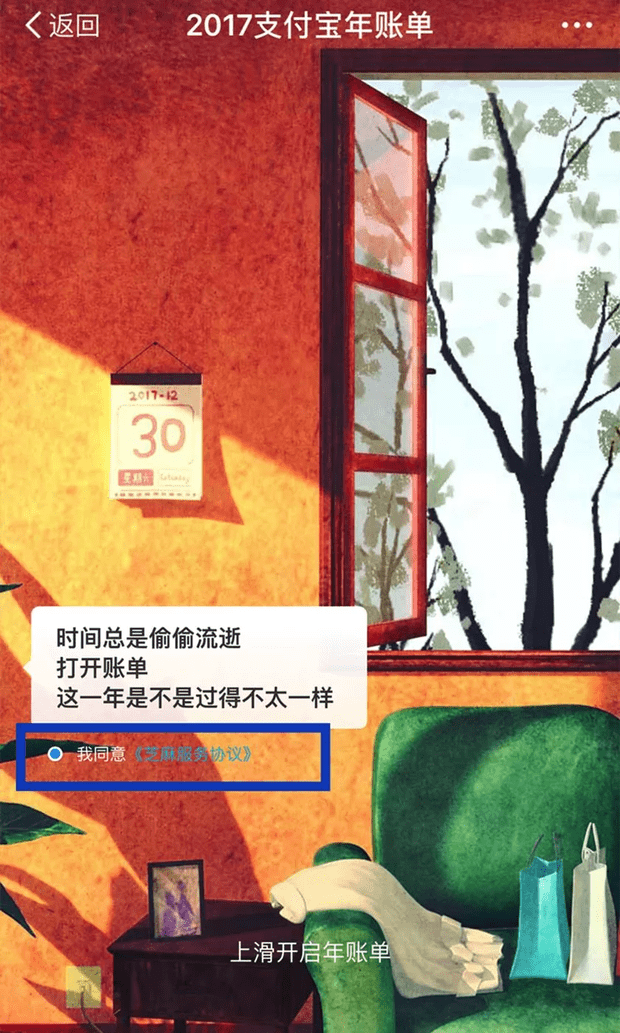不,我要发言

一边是刘虎被批捕、格祺伟被批捕、董良杰被批捕、董如彬被批捕……陈永洲被刑事拘留,一边是 “寒蝉”效应在余姚水灾中充分显现:“监测发现,对比今年芦山地震事件和去年北京7.21暴雨,新浪微博中‘余姚大水’的信息量为17万条,远低于‘芦山地震’的499万条和‘北京721暴雨’的61万条,同样,在抽取‘芦山地震’中表现活跃的50位意见领袖的微博,在此次余姚水灾中‘转发表示关注’的有27位,‘发表评论’的仅只有16位” (《大V退场,余姚水灾成“信息孤岛”》 作者: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 庞胡瑞)。然而,当灾难真相与美丽谎言之尖锐对立最终演化为宁波电视台采访车被砸、余姚人走上街头时,公众的质疑和愤怒在互联网喷薄而出!法不责众的镜像再一次映射出两高关于网络言论司法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的荒诞与不法。
在任何国家,因言治罪都是法治之耻,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之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各地因言被行政拘留、刑事追诉的人数不少——抓记者、抓大V、抓未成年初中生……但雷霆手段背后,假司法解释之名选择性报复执法、杀一儆百,以堵住公众悠悠之口、试图垄断话语权才是司法解释出台的真正目的所在。
两高司法解释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恶果是警察权在言论领域的滥用。
在我国,警察权习惯性扩张与异化并难以得到有效节制始终是个大问题。2000年掀起并持续十数年的“打黑”专项运动将警察权的滥用推向极致。发端于辽宁、在重庆达到巅峰的“打黑”运动中,全国各地警方广泛存在的公权劫掠、草菅人命、刑讯逼供、恶意构陷等严重问题,给诸多企业家和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甚至,为了服务“打黑大业”,原本应由检察院侦办的职务犯罪也往往被挂上“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检察官和法官被警察以打黑为由头、随意抓捕的情况并非罕见。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诉法》赋予侦查阶段律师的及时会见权和刑事拘留后24小时内必须将嫌疑人送交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对以刑讯“造案”为主要手法的“打黑”运动不啻为釜底抽薪,但在国家层面,至今未对“打黑”中存在的错误和不法有任何检讨与审视,更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有效追责。不仅如此,即便在福建吴昌龙、浙江张高平等个别非“打黑”冤案已经平反的情况下,也未见任何涉嫌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警察承担责任。
当习惯了异化和扩张的警察权在屡屡走偏后总能持一副“正确”的面孔全身而退时,警察权强力介入言论领域并作为裁判员大肆因言抓人并绑架检法出台司法解释为其背书的做法便毫不奇怪。按理说,逐渐被扩张和异化的警察权更需言论的监督与批评,但事实上,应被监督的警察权却成了判断公民是否因言入罪的“排头兵”,此种情形必然进一步导致警察权的扩张和滥用。这是司法解释带来的另一个死结,在这个死结中,民众灾难不会有终点。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拘,据说新疆警方也以同样的罪名抓了一个,该罪名虽然与此次司法解释没有直接关系,但没人能否认,这一系列案件是司法解释推倒的因言获罪的又一张多米诺骨牌,而且不会是最后倒下的那张牌。
另一方面,当诸多法学家、律师、各行各业有发言权的公民在司法解释面前为明哲保身选择沉默时,警方继续抓捕“勇敢发言者”并对其刑事追诉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肩负捍卫法律的人没有履行其义务:战场上,当一千个人必须迎战时,人们可能不在意某个人的逃逸,但当一百个人甚至数百人开小差时,忠于职守的人的形势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整个抵抗的负担全部落在了他们的头上。”(《为权利而斗争》,作者:耶林)。配合警方的,是全国“200万网络舆情监督员”全面出动,他们时刻准备着,用“贴身摔”的方式对任何质疑官方及官员的言论倾巢而出,以只讲论点不讲论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语言逻辑,对言论“幸存者”的理性讨论与真相探求一次次发动来势凶猛的集体围剿……抓捕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勇敢发言者”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沉默、或者生活在粉饰太平的谎言之中,掠夺者仍然掠夺,加害者继续加害……没有人能确保自己会在这场浩劫中侥幸脱身。
如果沉默并不能使我们保全,发言便不会比沉默使我们面临更多危险。
当余姚灾情十万火急、万众瞩目,诸多求助信息需从灾区传出,余姚警方却对“造谣”网友行政拘留时,当诸多灾民和救助人员想发布消息却担心落入两高关于网络言论司法解释的陷阱而保持沉默时,我曾在微博呼吁:我们有义务继续吁请当局废止该司法解释,我们有责任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然后坦率地说:不,我要发言。
是的,当《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权被司法解释几近剥夺,当警察对言论的审查随时成为剥夺我们自由的借口,当监狱成为每个人开口说话的下一步可能、恐惧占领我们的内心时,在诸多被因言追诉者孤独面对司法沦陷的当下,我们作为同类,作为真相之追寻者和真理之受益者,应该坦率地说:不,我要发言。
我们发言是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脱离苦难,因为多数人的沉默只会让被抓的“少数人”越来越多;我们发言是为了让抓捕者不再肆无忌惮,因为真相的阳光会让我们更加健壮而且更富勇气;我们发言是为了诉说我们曾经和正在遭受的屈辱,让懦弱者变得坚强,让勇敢者不再孤单。
我们不仅吁请两高废止荒诞不经、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的司法解释,以重获久违的言论自由;我们还吁请:不能让戕害言论自由的警方负责人如在“打黑”运动中一样逃脱追责,中央政府应正视警察权的约束问题,并将警方相关责任人撤职查办。因为,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容“警察说了算”。
附文:对两高关于言论司法解释的质疑与违法性分析
关于诽谤罪
司法解释第二条将诽谤信息被实际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或者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等情形,均规定为情节严重。该规定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有违刑法对犯罪构成应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尤其是,歪曲并无限扩大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等数种情况规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致使《刑法》246条第二款之外延扩大到无法判断,进而导致公民行使表达权、批评权时面临随时被刑事追诉的危险。
首先,何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否均为非法?在《刑法》未对群体性事件定义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论群体性事件是否合法,引起群体性事件的言论是否均应面临刑事追诉?
其次,公共秩序混乱的标准是什么?我国《刑法》第290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而司法解释竟规定“引发公共秩序混乱”便可治罪,言论行为人比扰乱秩序行为人入罪标准更低。试问:假如某言论导致公交车站排队秩序混乱,是否要对言论行为人治罪?
再次,民族、宗教冲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某言论导致一个维吾尔族人和一个壮族人吵架,或者一个基督徒把一个佛教徒打成轻微伤,基督徒被治安拘留,言论行为人是否要被刑事追诉?
第四,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有何共同点?即便有诽谤多人之嫌,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却放弃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插手的动机是什么?依据的“真相”是什么?受害人所做的描述是否等于真相?警察是否有权对真相作出判定?以记者刘虎案为例,网络举报3个高官,未见任何有权机关调查该高官,也未见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更未见几个高官的自我澄清和提告,而且刘虎举报所依据的证据来源和线索均有据可查,有权机关是否核实过这些证据和线索?公民对官员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披露和举报是公民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刑事追诉是为了打击报复还是为了保护贪腐?而且,刘虎被羁押前,司法解释还未出台。而为了使公安机关原先抓捕刘虎等人的行为师出有名,两高不惜自降身价,匆忙出台司法解释为滥用的警察权应景背书。
第五,何为国家形象?谁代表国家形象?何为恶劣的国际影响?代表国家的一国政府,只需遵守国际法、尊重公序良俗和国际惯例,尊重公民的各项权利,自会有良好的国家形象,本国公民的言论如何能损害国家形象?如果政府还有起码的公信力,如果真相总能在讨论中厘清,任何人的言论也不可能产生不良国际影响。反之,如果不让公民讲话,或者公民讲话时任意打压,时间久了,谬误和谎言将成为政府和官员的专利,而公众的任何质疑、追问和对真相的厘清都可能被当做“诽谤罪”所打压,这恰恰是真正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关于寻衅滋事罪
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对“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和“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须知,网络只是信息的媒介和载体,从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即便网络是公共场所,网络言论也不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须犯罪主体具有直接故意方能构成,而网络上无论是辱骂、恐吓他人、还是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行为人的直接故意只是辱骂、恐吓的故意和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故意,对破坏社会秩序和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结果即便有故意,也只是放任的故意,即间接故意,而间接故意不构成寻衅滋事罪。遗憾的是,不仅司法解释罔顾常识僭越立法职权作出如此荒谬的规定,而且,董良杰、董如彬、格祺伟等人均被检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
精彩推荐
- ·致中共赣州市委史文清书记的一封..2015-06-27
- ·致军委习主席的一封信2013-04-01
- ·就#衡阳周氏家族案#对衡阳中院..2015-11-27
- ·戴玉庆案:反腐还是报复?2015-06-05
- ·王甫:刑法修正案(九)或将导致..2015-08-29
- ·建三江困局2014-03-30
- ·司法打手 末路狂徒2012-08-31
- ·清明节悼念靖江司法2013-04-04
- ·致湖南高院康为民院长的一封信2014-03-27
- ·律师为谁辩护2019-08-12